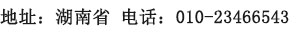严党的垮台标志着大明朝进入了清流势力的独霸时期。
然而,表面平静的政局下,暗涌仍在不断蠢动。
围绕权力的争夺永远存在,因为权力直接关系到资源与利益的分配。
总有一种矛盾占据主导,不是外部的就是内部的……
当外界威胁消失,内部矛盾就会逐步浮现,当下的政局亦复如是。严党一倒,清流派内部的斗争从统一战线转为了内斗。
这在高拱公开对徐阶的挑衅中表露无遗。
徐阶的“不沾锅”艺术
自从担任内阁首辅以来,徐阶对严嵩有了几分理解,在他看来,管理这个位置根本就是个苦差事。
国库空虚,需要资金的地方却数不胜数,军事、官员薪酬、民间救济等等都急需资金。
效仿严党敛财吧,嘉靖或许满意,但徐阶的名声就毁了,同时也会被裕王排斥,这种自寻死路的行为徐阶绝不会为之;不敛财吧,军事、官员、百姓的需求怎么满足,轻则职责不清,重则被指误国误民。
在此背景下,徐阶领导的清流派再度激励御史上书,建议嘉靖处决严世藩等严党要员,没收家财以缓解国库亏空。
资金虽解决,如何分配成了新问题。
嘉靖的意图,徐阶明了。
从嘉靖将其子徐璠安置在工部侍郎的职位上,徐阶便明白嘉靖的提醒——修建宫观的任务必须加快,否则首当其冲的就是他的儿子。
但眼下众目睽睽下的巨款,一旦徐阶稍有偏袒修建宫观的迹象,立刻就会被批为“迎合圣意,失于公允”,成为众矢之的,名声、威望、清誉皆将毁于一旦。
虽困难重重,但徐阶终究是徐阶,成功培养出被誉为“不沾锅”的赵贞吉,其甩锅卸责的能力绝对是一流的。
经过一番思量,徐阶提出了“两步走”的对策:
首先,将内阁内部会议拓展至与各部的联合会议,邀请时任户部尚书的赵贞吉和工部侍郎徐璠共同参议。
这么做的好处包括:
①多了一层保护。
不管商议出什么方案,都是内阁与六部共同的意见,而非徐阶一家之言,如此一来即便嘉靖不满,责任也不会全落在徐阶一人身上,同时嘉靖也会顾忌“民意”。
②多了两位盟友。
目前内阁仅三人,徐阶、李春芳、高拱。
李春芳以其“甘草次相”之名著称,一贯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准则,几乎不揽事也尽量不做事,任何事都让徐阶主导,因此徐阶并不担心李春芳会对他造成威胁。
但高拱不同。
高拱与徐阶同为裕王派的核心人物,地位仅次于徐阶。虽同为一派,但严党一倒,两人的矛盾日益明显——高拱的目标是内阁首辅之位。
高拱表面上对徐阶极尽敬意,严守下属礼节,但私下里却对徐阶的某些行为持保留态度,认为徐阶过于圆滑,缺乏担当。这一点,从高拱在裕王府质疑徐阶为何不敢在御前直言反驳严嵩的事就可见一斑。
问题的核心在于:
因为浙江贪腐案件,为了打击两大派系,同时保持权力平衡,嘉靖曾将严世藩、高拱、张居正三人一同排除出内阁。
现在严党倒台,理应高拱与张居正都能回归内阁,却只见高拱回归,张居正却未见踪影。
显然,这是嘉靖的有意安排。
原因也很简单:
嘉靖清楚,清流表面和谐,实则内部意见分歧,徐高张三人各有所图,安排高拱回归,正是嘉靖的帝王之术——用高拱来制约徐阶,就如当初利用徐阶制衡严嵩,避免一人独大的局面发生。
至于张居正,那是嘉靖留给他儿子裕王的后手。
对于张居正推行新政的志向,嘉靖心知肚明,但在他在位期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故意将张居正暂时边缘化,待裕王继位后,若想推新政,自然会重用张居正。
也就是说,目前能对徐阶形成威胁的只有高拱,唯一有资格对徐阶提出质疑的也只有高拱。
然而,徐阶心知肚明,内阁与六部的方案不可能以工部为主,这意味着方案极有可能被嘉靖否决,届时,高拱可能会借机攻击,质疑徐阶作为清流领袖、内阁首辅,却不敢为天下百姓争一争。
为此,徐阶让赵贞吉与徐璠加入,实则是为了多几位盟友,在必要时刻为他辩护,确保一旦高拱挑战,能有人分担压力,为他挡箭。
毕竟,以徐阶的地位,直接与高拱冲突既失了份量也失了面子。
徐阶的第二步则是:静以待动,明知方案会让嘉靖不满,依然按众意将方案提交给嘉靖,过程中不表达任何个人观点。
这样做的优势是:
将问题和恶名推给上面——嘉靖若对方案不满,那是他的事,到时我再顺势解决,反正坏名声我不背。
如此一来,修改方案时也有利于保全自己的清誉——徐阶绝不是只会谄媚领导的人。
果不其然,方案一提交即被嘉靖婉转驳回。
当徐阶持票拟回到内阁时,众人皆起立,目光集中于他。
批准与否,大家皆等待徐阶的回答,然而徐阶自进门起便沉默以对。
于是,急切的高拱开口询问:
“阁老,皇上未让司礼监盖章吗?”
官场有其规矩,上级未开口或未示意,下属无权越级发言。高拱直接越过次辅李春芳提问,显然违反了规矩,这也间接说明了两点:
一是,李春芳在内阁的发言权并不高(这正是“甘草次辅”乐于见到的情况);二是,高拱根本不将李春芳这位上司放在眼里。
换句话说,新一届内阁成员中,李春芳名义上虽排第二,实际的“副手”却是高拱。因此,高拱的先发制人在场的所有人都视为理所当然,无人感到意外。
见徐阶只是叹气不作回应,高拱更为焦急,追问道:
“徐相,京内外官员的欠薪,南北战事所需军饷,以及数省灾民救济等等,都已批准了吗?”
注意到高拱对徐阶的称谓变化,从“阁老”到“徐相”,后者明显带有“公事公办”的语气,也就是说,高拱在强调事情的紧迫性,试图迫使徐阶尽快给出回答:
作为首辅,明知问题的紧迫性,都等着用这笔钱解决问题呢,别再故作深沉,快点给个明确回复吧。
终于,徐阶回答了:
“吏部的欠薪、兵部拟定的军饷,以及受灾省份和过重赋税州府退还百姓税收的申请,都已经批准。”
明显的上位者的言辞:只说了一半,其余靠听者自行理解。
听到徐阶提到吏部、兵部、户部,却唯独没有提到工部,高拱立即意识到问题出在了工部的预算上:
“工部为皇上修建的工程,还有户部拨给宫内用款的申请,未获批准?”
得到徐阶的确认后,急于了解原因的高拱又问:
“难道是皇上认为给宫内拨款太少了吗?”
面对这种直接涉及嘉靖的问题,谨慎的徐阶自然不会轻易回答,而是选择了沉默。
此时,次辅李春芳终于开口:
“若这两项未获批准,之前的三项批准也等同于无效。”
显然,李春芳在试图缓和紧张的气氛。
高拱提问,徐阶不回应,气氛一度僵硬,赵贞吉与徐璠作为非内阁成员,若李春芳不开口,他们便无权插话,因此李春芳不得不接过话题,以继续对话。
内阁三人均已表态,赵贞吉此时可以发言,他立即将问题转移到海瑞身上:
“敢问徐相,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例如海瑞在六心居妄议皇意,导致皇上不悦。”
在御前,因海瑞而起的疑虑已使嘉靖对裕王产生怀疑,赵贞吉不知情,但徐阶了然于胸,见弟子不时宜地触碰敏感话题,立刻制止:
“勿需无端猜测。”
赵贞吉的错误答案后,徐璠接着发言:
“归根结底,还是宫内拨款实在太少,父亲,可否让儿子将昨日未尽之言继续。”
徐璠身为徐阶之子,言辞谨慎,不露痕迹。
他未如高拱直言嘉靖“认为钱少”,而是另辟蹊径——“拨少了”,表面意思相近,实则大相径庭。
“嫌少”意味着嘉靖无理取闹;“拨的少”则指责内阁与六部不作为。
如此一来,即使内阁的讨论传到嘉靖耳中,嘉靖也不会对徐家父子不满。
徐璠的处置,徐阶颇为满意,但有些面子上的事必须做到位,以防被人抓住把柄,因此徐阶表面上批评儿子:
“讨论国事就讨论国事,何来父亲儿子一说,此处乃内阁。我已多次提醒,到此你只是工部侍郎。”
众所周知,领导在众人面前批评自家人,多半是作秀,要么是为了显示公私分明,要么是借机警示他人。
徐阶这番话既是,同时也在告诉在场众人,徐璠接下来的发言,完全基于工部侍郎的立场,提出的问题也是出于职责所在,与他徐阶无关。
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徐璠没有徐阶的默许,或是未与徐阶事先沟通,他又怎敢轻易表达意见。白话来说,徐璠接下来的发言,无非是徐阶借儿子之口,间接提出问题:
“工部负责的皇宫工程已施工逾两年,尚未完成一半。朝天观与玄都观的扩建自去年打地基至今仍未完工。如今已七月,需用的石材须在冬季前运抵京城,若再不足额拨款,明年工程仍难以完工。工部难以交差,内阁责无旁贷。昨日已言,近千万银两中,仅拨给工部一百六十万,既需修宫又需建观,所需材料均为大理石、花岗岩及红木、檀木,怎算也少一百五十万。”
这些话,徐阶不能说,一旦说出便有所偏袒,有所偏袒就会损及清誉。毕竟身旁还有个随时准备挑战的高拱,因此徐阶特意让徐璠参与会议,从工部的视角将问题摆到台前,再随机应变。这也是他让徐璠参加会议的一个原因。
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说出,含义大相径庭。有些人可以说,有些人不可说,有些人说出来是别有用心,有些人说出来却是客观论事,归根结底,立场和处境决定了言论的性质。
这道理,类似于胡宗宪让赵贞吉上疏阻止郑何二人变卖沈一石家产时的那句话:“你上疏,即便出自私心也算公心,我上疏,纵有公心亦被视为私心。”
徐璠言毕,徐阶直接将问题抛给了旁的李春芳:
“李阁老,对徐璠的话有何看法?”
作为领导点名,李春芳必须发表意见。
达到这一层次,每个人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李春芳心知肚明,徐阶此时把问题交给他,正是希望他顺着徐璠的发言继续下去,于是,他顺势而为提议道:
“是否可以再详细计算一下。看是否能在这几项开支中,再挤出一百五十万银两给工部。”
李春芳话音刚落,对方案被否决一事已然不悦的高拱,立刻反问:
“资金明明就在这里,那你能不能提出个方案,是削减官员的欠薪,还是减少军事开支,抑或让灾区民众与百姓饿死?”
表态虽无成本,提建议却需负责。李春芳哪里愿意做这个决断,避而不答:
“我只是说能不能再仔细算算。”
我只提议仔细计算,未说一定要这么做,总之决定权不在我,你们商量好了,我跟着意见就行。
李春芳虽名为次辅,高拱再怎样不屑也不好一直追究,便将矛头指向提出问题的徐璠:
“那你们工部怎么说,减掉哪一块给你们。”
徐璠亦非易与之辈,见高拱将“锅”扔给自己,一语回绝:
“回高大人,下官只负责皇上宫内工程,这些自应由内阁与户部斟酌讨论。”
不归我管,我只从工作角度提出问题,至于如何解决,那是你们领导层的事,与我无关。
见状,高拱义愤填膺,直言不讳:
“怎样斟酌,怎样讨论?国事如此紧迫,我们还在此纠缠。我负责吏部,不论外省,仅京城官员已有不少人在米行赊粮半年,更有欠租之苦……更何况兵部,俞大猷、戚继光在福建、广东与倭寇浴血奋战,蓟辽总督处亦战事紧张。赵大人主管户部,昨日也言,若干灾区与苛税地区恐将引发民变。如今我们争论不休,仅为工部,仅为修建宫殿与道观。”
“徐相,作为内阁首辅,应当在皇上面前力争一争。我们这些大臣,应当对得起大明江山与天下百姓。”
见弟子向师傅挑衅,赵贞吉不忍旁观,出于情感与前途考量,作为弟子的他此刻必须为师傅辩护,于是在不需徐阶开口前,赵贞吉便反驳道:
“高阁老,我对此表示不同意。你怎知徐相未在皇上面前尽心进谏?若论争,高阁老您可以上书,我们都可以。春秋责贤者,但徐相一人怎能承担大明江山?”
意思是:你高拱有能力,有勇气,不畏惧得罪嘉靖,你上书争取啊,别在这里光说不做。
高拱听懂了赵贞吉的潜台词,立即反击:
“那我们一起承担!我高拱现在就写奏折,你赵贞吉也一并写,六部九卿,众多给事中与御史均可以上书……笔墨就在这里,赵大人,我与你一同上书,你敢吗?”
你说我不敢争?好,我们一起上书,你别在背后只说不做。
此时,赵贞吉当然不能示弱,哪怕不情愿也要硬着头皮前行:
“只要对大局有益,你高阁老忧国忧民,我愿意陪同。”
高拱的挑战,本在徐阶预料之中,也正因为要避免与高拱直接冲突,徐阶特意邀请赵贞吉与徐璠参与内阁会议。
因此,赵贞吉与高拱的争论中,徐阶始终保持旁观,但当两人争吵升级至上书一事时,徐阶不得不中断:
“现非抱怨之时,任何人都不得上书,更不可私下议论朝政。”
随后,面对高拱的不满追问,徐阶提出了无法反驳的理由:为了大明朝的长远未来。接着缓缓叙述了御前发生的三件事:
①嘉靖命裕王抄写海瑞所提字句刻匾(嘉靖已对裕王产生疑虑,我们再上书只会加剧裕王的不利)
②冯保被驱逐出裕王府(现在你知道我为何不敢争了吧,嘉靖连孙子都“打了”,我若再争,便是动摇大明根基)
③上午奏对时,嘉靖两度不适(嘉靖身体欠佳,若因我们而气绝,我们的九族都得下地狱报道)
至此,高拱还能说什么,只能默听徐阶最终的安排:
“近日通告各部,告诫属下,大家须以国事为重,禁止上书,禁止私议朝政。”
同时,赵贞吉与徐璠,已完成使命的两人,也被徐阶送回了各自部门。
结语
为何赵贞吉被誉为“不沾锅”,如今可谓洞若观火。
论起敛财,徐阶不及严嵩,但谈及甩锅卸责,徐阶几乎无人能敌。
为了化解高拱的挑战,为了维护自己的清名,为了彻底摆脱责任,连亲儿子与门下弟子都成了徐阶用来操作的“棋子”,一个负责“演恶人”,一个在前线作战,他则静观其变,时而扮演无辜者,时而充当调停者。总之,徐阶必须成为大明朝最清白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