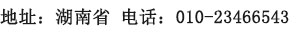记得有一次和我主任聊天,不可避免的聊到工作上的事。(好像我们经常这样)
我说,诶,主任,那个卵巢癌肺转移的给我打电话了,ta说儿媳看ta肚子又鼓起来了,但ta自己又说没有涨感。我让ta去查一下彩超和平片。你说大概能挺多久又得住院,一个月?
主任:可能半个月。就是抽水、放水、流失蛋白、补蛋白,继续抽水放水再补,循环往复,最后瘤子越来越大,人也就干巴没了。
我:别的办法呢?手术?
主任:晚期多发转移了,意义不大,救不了命了。
我沉默,打算换个话题,但后来发觉这个话题转移的并不是很好:我想起那个姓曹的了,记得吗?去年,50多岁,半路夫妻那个。那天我夜班,你半夜过来,刚到屋人就抽了,边抽边吐,抢救两个小时人没了,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患者死掉,我一连很多天下班回家就哭,没办法控制自己。
主任:姓曹?哦,信佛那个,想起来了。你有感触好啊,我已经麻木了。
我:看开了。
主任:不是看开,你说的是境界达到了,我是麻木。我觉得他们都该死。(人到该死的时候就死掉了,自然淘汰)
我沉默,关于麻木,想到父亲曾在饭桌上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感性没办法改变一些事,太愧疚是做不好医生的。于是似乎理解了这样的麻木。
我等他继续说。
果然,我的主任接着道:感触最深的一次,那时我刚工作没多久,就像你这么大吧。有一个大学刚毕业工作的小伙子被情敌用刀扎了,到医院人就已经不行了,血性气胸,失血太多太多。他母亲抱着他,撕心裂肺的嚎,把我们所有人都听哭了,她那种哭声我确信是真的,因为她只有那一个儿子。剩下的,我觉得都是假的。
我不置可否,因为对待这样的事,非亲身经历是很难体会其中滋味的,于是我只能不置可否,而接下来的话,则完全受自己好奇心驱使,我问:还有吗?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听众不止我一个人,因为印象深刻,放在这里会很恰当,我就把它写在一起吧)
主任几乎没怎么迟疑:医院进修的时候,有个小女孩,十三四岁,恶性肿瘤,化疗后她母亲带着她来医生办复查,我推着她去拍片,看到她头发稀疏的根本不像一个花季的少女。电梯里,她说妈妈妈妈,我是不是好了,你看我都瘦了,我能穿漂亮裙子了。哎呦我,操他个妈,给我整的鼻子酸,眼泪直打转。
我特意看了一下他的眼神:中年男人,坚毅都是在眼神中体现出来的。日夜工作接触,便蕴生出专属于外科医生间的默契和情谊。彼时的沧海桑田,此时便如同管中窥豹,只一双目足矣窥见一般。但是那一刻,他的眼神却如水流潺潺,格外温柔。
我仍不甘心,继续追问道:那个半路夫妻呢?抢救那个,你觉得他们算么。
主任:哦,也算吧。
这是我人生第一个主任,一年前我们共事,他教我本事,和我父亲同岁,五十知天命。正直,局气,务实不虚,只是真诚又执拗的做着自己该做的事,工作一年,我确信许多人忘记了誓言,许多人,但不包括他。直到现在我在他身上看到的宝贵品质,远远比我们初识时多得多。
外科医生们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曾用不同的思绪面对同样的问题——死亡,因而混淆了灵魂。
然后死亡的昙花终于一现,生命的臭味开始相投,宿命令我们乐此不疲,好似上瘾般的投入其中,却永远不知何谓始,何谓终。
我喜欢这个行当,而当我意识到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时,我便爱上了这种感觉:也许,我的余生还会见证许多死亡,然后再跟随他们不断死去,找到自己的出处。
图一为去年三月入职第一天参加的阑尾切除手术,左一是我主任,图二他位于右一,我想我绝不该忘记他。
图一:
图二:?切掉的阑尾,青紫肿胀:?他送给我练手技的止血钳和持针器,几乎与我同龄却如崭新出厂:?第一次练习缝合白衣,很丑哈哈:??第一次巨型白线疝缝皮(超过30cm),手术是院长参与指导,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外科团队带来的巨大成就感,手技仍有许多不足:?感恩这一切,放一张去年独自包揽一节车厢的帅帅的我,希望自己变得更好????????PS: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